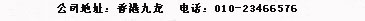风起心静关于三线单位居民生活区研究的心路
文
辛文娟
每当风起时,我都会感到内心分外平静。因为风让我想起北方的故乡X省S市。S市本来是一片籍籍无名的大荒滩。年,新中国煤炭工业部成立了S市煤矿筹建处,计划将S市所在地建设成为新中国重点建设的十大煤炭生产基地之一。整个S市下辖两个新中国重点建设的矿务局,其中一个是成立于年的国家焦煤基地B区矿务局。后来随着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全面实施,国家加强了对工业体系的投资、大力推进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建设。在这个背景下,自年起,S市的煤炭开发事业迅速拓展与加强。
我就在B区矿务局下辖的第三煤矿(简称三矿)出生并长大。三矿人开玩笑说,我们那里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因为大风总是刮啊刮,所以宁静的三矿大院里,总是处处可见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煤尘。
在我读小学时,父亲有位挚友,是三矿办公室主任,我叫他车伯伯。车伯伯清瘦儒雅,家里书多。在当年封闭的矿区中,想找些课外读物不太容易。我经常跑到车伯伯家看书或借书。车伯伯每次看到我,总是像对待大人一样,温和地跟我聊天。有一次,车伯伯很认真地跟我说:“等你长大了,要好好写本书,讲讲咱们矿区的生活,这里真是故事的宝藏。”车伯伯应该对我说过很多话,但是我现在唯一能记起的,就是这句话。
一、在MarstonHill思念三矿
原三矿居民马丽媛女士绘制的三矿办公区素描图
年12月,我还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有一次汇报课程作业选题时,我向恩师单波教授谈起三矿变迁的故事。当时我着重谈的是矿区移民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问题。单老师建议我可以试着在家乡做一次调研,不要带着预设和偏见,去田野寻找“真问题”。年1月,我放寒假回家,开始试着做调研。当时我首先选择的社区是QJ社区。因为这里是三矿居民搬迁之后集中居住的其中一个社区,我的大家族成员主要集中于此。我的访谈是先从大家族成员开始的。但是我很快意识到单一的一个社区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因为在访谈中,很多人都会提起三矿居民集中居住的另外一个社区——NZ社区。他们会把QJ社区和NZ社区做对比,认为分别居住在两个社区的居民,目前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差别很大。于是,我赶往距离QJ社区约17公里的NZ社区进行了初步调研。当时访谈了一些我们过去的熟人,包括邻居、我父母的同事等。如果说在QJ社区做调研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那么在NZ社区,我这体会到了那里居民的切身之痛:寒风瑟瑟的冬日,很多居民家里的暖气不热,我在室内做访谈时,不敢像在QJ社区居民家那样自然而然脱去羽绒服。很多居民家的洗衣机居然只是摆设,常年不用,因为物管一天只给送三次水,且每次送水不到一小时,水流细小,而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在三矿时,用洗衣机洗衣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怎么进城了,反而不用洗衣机了?晚上7点之后,天彻底黑了,走在巷道里伸手不见五指,这与QJ社区夜晚的灯火通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访谈过程中,我明显感觉生活在这里的三矿人,怨声载道情绪低落,提到“NZ人”这个身份都很懊恼。无论跟他们谈什么话题,最终都会落到“NZ社区简直没人管了”的话题上。每次到NZ社区做访谈,我的心情都比较沉重。这使我想到,应当把两个社区进行对比研究,分析造成居民生活状态迥异的背后原因。年5月,我根据在家乡的调研,完成了一篇约一万字的课程作业,以“身份认同”为研究主题。这是我在家乡做调研时,发现的很多问题中,一个比较好切入的研究点。但是真实的社区调研经历告诉我,家乡还有太多问题值得思考。
NZ社区居民在家中的日常生活图
QJ社区居民在S市老年大学上乐理课
年7月,我们几位同学随单老师赴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JensAllwood的自家山庄MarstonHill参加跨文化暑期夏令营。临别前的一个午后,我在Allwood教授家一个位于小木屋里的图书室里独自呆了几个小时,翻到了他祖父和父亲的传记,里面讲述的关于这个山庄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和人物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当我读完这些传记后,我才真正明白我到底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听一个什么样的人讲课,暑期的课程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很快,我进行了文化反思:我的家乡呢?那里更有惊心动魄的创业史,有祖辈们留下的家族故事,有天南海北的新中国工业移民在那里交流融合的故事,有资源枯竭后工业移民长时间大规模的迁移故事。但是,我对那一切的了解却是很浅显的。于是在年8月回国后,我下定决心,博士论文的选题,一定要与家乡居民的交流故事有关。很幸运的是,恩师单波教授支持我的选题。年10月,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顺利通过。
二、田野工作的展开
年12月底,我开始了在家乡的田野调查工作。在预调查阶段,一次偶然与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叙旧时,她谈到她娘家在JL社区,那里是三矿居民集中居住的第三个社区,而她则在QJ社区居住。她说很奇怪,每次到了JL社区,就能感到轻松愉悦,因为那里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儿,邻居之间很容易就交流起来。但是怎么一回到QJ社区,这里就充满了客气与防备的感觉。这次谈话使我敏感地意识到,JL社区有可能具备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于是,我通过父亲介绍,与JL社区的几位居民和社区居委会主任取得了联系。在初步访谈之后,我认为JL社区的确值得纳入到我的田野点里。因为这是一个七矿合一、矿区人口高度集中的社区,它建成时间最晚(年主体住宅楼修建完毕),居民城市化融入程度尚不深,较好地保存了一部分老矿区居民的生活和文化交流模式。在预调查阶段,我建立了与JL社区一些居民的初步情感联系,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得了更多社区中文化精英的联系方式,为我后期的正式调查提供了大量珍贵线索。
JL社区秦腔团部分成员在地下车棚改造的秦腔剧场化妆
预调查之后,我确定了我的三个田野点:NZ社区、QJ社区和JL社区。这三个社区是X省原B区矿务局三矿居民在矿山企业破产之后,分批迁往的三个城市社区。这三个社区住房性质丰富,包括住房改革之前的单位福利房、首批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国家特殊政策安置房。不同性质的住房代表了中国城市市场化转型不同阶段的制度性因素,是制度在空间上的固化。社区居民所属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也差异很大,通过对不同社区中居民的空间行为的比较,能够反映出转型期中国经济制度转变对城市空间重构及居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影响。
根据我的研究问题,我确定了研究方法应该是“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ethnography),即在多个田野点展开调查研究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G.Marcus)[1]在传统单一地址民族志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发展多点民族志,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来推动人类学成为一个适应当代社会的学科。[2]他所说的多点民族志即“通过连续性的叙事和共时的效果,民族志作者可以尝试在一个单一文本中来表现多重的、随机相互依存的场所,对每个场所进行民族志式的探索,而这些场所又通过发生于其中的行动的预期和非预期的结果联系在一起”[3]。马库斯曾指出,过去的民族志研究对象往往是传统的单点场所(single-sitelocation),可是这些场所目前都处在更宏观的社会结构背景下(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因此,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已将开始转向我们可以观察和参与在其中的多点场所(multiplesites)。这样,我们将本地与全球联系起来,将生活世界与世界体系联系起来。[4]通过在多个地点展开调研,可以看到文化意义、人、故事等在不同空间中的流动状态。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移民、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等在城市中聚集,流动于不同的空间中。多点民族志由于更加重视从宏观体系视角来研究群体的流动现象,因此,在研究分散、迁移的研究对象时,这种方法尤为合适。
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导下,我于年12月至年5月期间完成了我的田野工作,使用了多种调查方法搜集定性资料,
转载请注明:http://www.592taotaole.com/bmdzlbf/109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