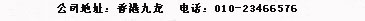沙俄侵华历史盘点从甲午战争的调停到
引言
掠夺中国金矿等资源,是沙俄加强扩张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沙俄统治阶级一贯垂涎于中国东北丰富的金矿等资源。在八十年代,他们一方面公开向清朝政府提出申请,甜言蜜语地要求租地开矿。一个名叫萨比汤的人,就曾聚集沙俄一批官僚、资本家,以“不在地方安集居民,亦不建造房屋,将来租约期满,仍将地段所建一切工程俱让还中国,毋须偿价,如饬令平毁,亦无不可”等好话,企图诱骗清朝政府租给粗鲁海图卡内一片土地,“开采金石各矿”。
另一方面,他们不等清朝政府回复,就暗中怂恿俄国人违约潜入中国境内,在根河、漠河、乌伊河、苏里河、兴凯湖、绥芬河,直至珲春附近漫长的边境地区盗采金矿。在越界盗采的人中,有流氓、冒险家、退职官吏和工商业资本家,他们身份虽有不同,目的却是一样,就是到这里“一攫千金”,成为暴发户。这一带地区黄金的藏量十分丰富,如在漠河一带,一千六百多市斤金砂,经过粗略淘洗,就可以获得约二十三两黄金。因此,盗采金矿的沙俄冒险家、资本家往往迅速发迹,盗采的规模不断扩大。
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沙俄一个名叫谢列杜金的冒险家,得悉漠河地区的赛泰有金矿后,就派矿山技术人员带领工人潜入当地进行采掘。据沙俄财政部记载,该矿区开始时仅仅几百人,“每天采掘到三十俄磅至一普特”金块。正因为这样,沙俄侵略者不久竟然将“赛泰”这个当地鄂伦春语意为“金属”的地名,偷偷改为“若尔托加”-俄语意为“黄色”。到同年六、七月间,若尔托加金矿的名字,已传遍沙俄阿穆尔省、后贝加尔省,形形色色的罪犯、商人和官吏趋之若鹜,工人也迅速增加。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春达五千至七千人;一八八五年一月(光绪十年十二月)激增为一万五千人。沙俄侵略者还组织探矿队,恣意扩大矿区。在来不及采掘或无力经营时,他就任意把矿坑出租或拍卖,把中国的神圣领土和宝藏视为私产。他们甚至擅自在矿区设立“采矿事务所”,建立行政机构;私设法庭,颁发法令,组织军队。如若尔托加矿区就有所谓“推选”的总首领,负责整个“采矿事务所”的行政和一般刑事案件的处理。“事务所”下辖若干“区”,由“首领监督”两人负责。矿区在平时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的武装队伍,俨然“国中之国”。
沙俄统治阶级除了有组织地掠夺中国的矿物资源之外,还一步步蚕食中国领土,不论公开请求租地开矿,还是暗中怂恿越界盗采,都是如此。八十年代中期,清朝驻俄公使刘瑞芬就曾指出:沙俄官绅要求租地开矿,是“始而租赁,继而图占。”萨比汤等人在粗鲁海图卡内所要租借的矿区,实际上已将“举凡内兴安岭阴之一带山河,包括无遗”。正是为了造成侵占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沙俄才怂恿掠夺者潜入中国。
沙皇政府甚至在边境城镇设立“收买金块事务所”,为这批掠夺者提供便利。这样,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金矿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进行掠夺性的贸易,是沙俄加强对中国扩张活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八、九十年代,沙皇政府进一步利用由不平等条约攫取的通商特权,对中国东北扩大商品倾销和廉价收购原料、粮食。沙俄对华贸易是不平等的、掠夺性的。沙俄工业品质量低劣而价格昂贵,一把铁斧在外贝加尔地区售价约五卢布,输到中国东北却要十二卢布。
沙俄廉价掠取中国的农、牧、林、矿等产品,加工后又高价向中国销售,牟取暴利。沙俄在中国边境地区,还享受免税贸易的特权,大量商品流入中国都不纳税,而中国物产输入俄国却要交纳很高的关税。九十年代,输入俄国的中国商品的关税率,等于商品价值的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百,甚至更高。其中,对中国原料的课税特别高。九十年代,沙俄通过西伯利亚边界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平等贸易,据估计总额在一千七百万至一千八百万卢布上下。
随着对中国东北经济扩张的加强,沙俄的纸币也渗入两国交界的中国边境地区,破坏甚至操纵了中国一些边境地区的金融。在中国东北地区,“俄国的纸币自由流通于瑷珲及其附近地区,在墨尔根、齐齐哈尔及三姓市也可以流通”。中俄在大黑河屯通商,“多以俄帖(即纸币)交易,而中帖则不行也。”沙俄纸币在“黑龙江城境,悉通用之”。沙皇政府还利用扩展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运事业,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和掠夺。
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成立的“阿穆尔轮船公司”,到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已拥有二十艘轮船和五十艘驳船,垄断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航运。沙俄还反复向清朝政府要求取得内河航行权,屡次侵入松花江进行掠夺。一八九三-一八九四年(光绪十九年-二十年)间,沙俄建造了一艘专供行驶中国松花江的轮船。它从伯力到中国吉林往返一次,沙皇政府就由国库拨给一千七百卢布的奖赏。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沙皇政府集资二百万卢布,成立“阿穆尔商船公司”,每年给予二十五万卢布的补助。这年就有四十六艘轮船和六十四艘驳船,航行于黑龙江、乌苏里江,并多次闯进中国内河松花江。这些船只运来布匹等工业品,高价向中国销售,又从中国廉价掠取粮食、牲畜和各种原料。沙俄就这样把中国东北的江河,变成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渠道,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沙俄对中国东北边区进行扩张的结果,不仅使这些地区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而且还通过这些地区一步步向南伸张势力,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面临黄海、渤海的辽东半岛。
正当沙皇俄国逐步强化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活动的时候,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沙皇政府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大搞外交投机,加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朝鲜与中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沙俄早就对朝鲜半岛怀有野心,想把它并入“俄罗斯帝国”,以便从陆上和海上进一步向中国扩张,变朝鲜为沙俄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桥头堡。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即沙俄吞并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不过五、六年之后,沙俄军舰就闯到朝鲜元山津,要求“通商”及准许俄国人在朝鲜居住。一八八四年,沙俄强迫朝鲜签订通商条约,获得通商、居住等特权。一八八五-一八八六年,沙皇政府多次诱惑朝鲜国王签订密约,企图将朝鲜置于沙俄控制之下,成为它的保护国。沙俄的这一阴谋虽未获逞,但它在加强向中国东北扩张的同时,一直虎视眈眈地注意着朝鲜,寻找机会下手。
一八九四年一月(光绪十九年十二月),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日本政府怂恿和诱骗清朝政府于六月共同出兵镇压。日本军队源源开进朝鲜后,拒绝清朝政府的撤军建议,并于七月二十三日突然在汉城攻击朝鲜王宫,建立了亲日傀儡政府。七月二十五日,日军又在海上袭击中国军舰和运载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正式发动战争。所有这些事件,都被沙皇政府利用来加紧插手朝鲜,力谋实现它一贯追逐的目标。早在甲午战前四个月,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便在致外交大臣格尔斯的急件中强调说,在朝鲜行将发生的冲突中,“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
五月下旬,由亚历山大三世亲自批准,沙俄“朝鲜人”号炮艇擅自开进仁川,密切监视局势的发展。六、七月间,当日本拒绝从朝鲜撤走军队、积极准备发动战争时,沙皇政府便以“调停”为幌子,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当时,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向清朝政府表示:俄国与朝鲜为近邻,“断不容倭妄行干预”,希望清朝政府与俄国“彼此同心力持”。他们还声称:俄国已“勒令”日本“与中国商同撤兵”,日本如不遵办,俄国准备“用压服之法”。沙皇政府还向清朝政府正式作出将“对中国持有最友好的态度,并将竭尽一切以支持中国的和平愿望”的诺言。
这一切,正如他们自己一再说的,主要是为了赢得清朝政府的好感,使清朝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沙俄身上,增加对沙俄外交上的依赖,不致转而向英国政府求助。在“调停”的烟幕下,沙俄一面怂恿日本侵略,一面伺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它积极支持日本关于改革朝鲜内政的恶毒策划,要求日本承认俄国参加这项“改革”的“权利”。因为实行这项“改革”,“将摒除中国在朝鲜的优越势力”,对俄国与日本“均极有利”。对于从朝鲜撤兵的问题,沙俄虽向日本提出过这个要求,但当日本向它表白“无意”占有朝鲜,愿意尊重俄国在朝鲜的“利益”时,它便复照声称“甚为满意”,暗示日本可以拖延撤兵的期限。这表明,沙皇政府所谓“调停”,实际上是想通过暗中支持日本,阻止朝中两国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互相支持,从而逐步取得在朝鲜的独占地位。
恩格斯曾说:“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一针见血地指出沙皇政府借“调停”为名,利用日本发动战争的野心所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沙皇政府立即表示“不干涉中日战争”。沙皇政府在“不干涉”的名义下,暗中与日本勾搭,只要有可能,总想把日本拉过来,作为争夺远东和太平洋霸权的帮手,免得日本被英国拉过去,成为英国的盟国。德皇威廉二世当时嘲笑沙俄对日本的“极力拉拢”,是“打算取得日本的欢心”,反映了沙皇政府的实情。
然而,日本侵略军在战场上很快取得优势,从一八九四年八月(光绪二十年七月)到年底短短几个月中,不仅占领了朝鲜全境,而且侵入中国东北。这就打乱了沙俄原来的整个阴谋部署。沙俄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一局势。它特别不能容忍日本向中国东北伸手。因为这样一来,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主要目标便不能实现,占有不冻港的宿愿也将落空,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美梦势必破灭。因此,一八九五年二月一日,根据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令,沙皇政府就甲午战争问题召开第二次大臣特别会议,重新考虑沙俄对甲午战争的后果应采取的态度。
会议主席亚历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在会议开始就指出,自从去年八月二十一日特别会议以来,“情况业已急剧变化,而日本接连的军事胜利,今日使人担心上次会议中根本不能预见到的中日冲突的那些后果。”会上除了讨论是否要出兵占领朝鲜半岛南端的巨济岛以控制朝鲜海峡外,着重讨论了中国渤海湾的形势。
会议最后确定了沙俄所应采取的方针:一,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使之“尽可能较日本为强”;二,同英法等达成协议,如果日本对中国谈判的要求“侵犯”俄国的“重要利益”,三,“则对日本施以共同压力”。所谓俄国的“重要利益”,是指朝鲜和包括渤海湾的旅顺、大连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只要日本在谈判时不要求占领朝鲜和中国东北及其港口,沙俄就可以继续保持“公正的中立态度”,否则,它就“不能置之不理”。
同年二月八日,沙皇政府正式决定它与英、法、德等列强接触,酝酿所谓“联合调停”的态度:如果日本的“议和条款是温和的,那时列强只能对中国施以压力,强迫中国接受”。这里所说的“温和”与否,主要是以日本对待中国东北地区和渤海湾以及对待朝鲜的态度为转移。二月十七日,日本密告俄国,同意清朝政府派遣全权使节,在朝鲜“独立”、赔款、割地和缔结新的通商协定的基础上,赴日媾和。虽然日本对割地问题仍然含混其词,但是,俄国却连忙于二月二十四日复照日本政府,说它保证“当能劝告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亦能劝诱其它强国”同俄国“采取同一方针”。
一八九五年三月(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上旬,日本侵略者又大举进攻辽东的清军据点,全部占领辽东半岛,直逼京津地区。同年三月二十日,清朝政府和日本谈判开始。日本占领中国辽东半岛,使它同沙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中暂时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对沙俄在远东的侵略计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时,沙俄感到日本崛起已成为自己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区域霸权的劲敌,便撕下“中立”的假面具,而“积极行动”起来。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沙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都主张趁中国危急的关头,扩张沙俄在远东的版图。
四月八日,沙俄把它反对日本割占中国辽东半岛的态度通知德法等列强,并征求它们的意见。四月十一日,沙皇政府又一次召开特别会议,对当时的远东形势进行分析,认为列强正准备瓜分中国,如果俄国现在就采取行动,占领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其它列强将会同样行动而导致新的冲突,在俄国还没有力量马上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利的。但是,由于日本占领中国辽东半岛,构成了对俄国的“直接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如把朝鲜南部让给日本,我们占领朝鲜沿海任何一个口岸,比容许日本人进入满洲更为有利。”
沙皇政府估计,一旦日本在辽东半岛站稳脚跟,将会侵占中国其它部分,“数年后天皇便成为中国的皇帝”。换言之,中国就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其结果,俄国要吞并中国、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野心不但不能实现,反而势必同日本发生更大冲突。因此,他们决定,与其等待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再采取措施,“为自己取得报偿”,不如这时就积极行动,发表“坚决声明”,逼迫日本从辽东半岛退出;同时让海陆军做好战争准备,万一日本不同意,就采取“坚决行动”,命令舰队轰击日本港口,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这样,既教训了日本政府,使它听从俄国,又能使清朝政府把俄国看作“救星”,“尊重”俄国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的方式”,修改中俄两国的“国界”。这样,沙俄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割占中国东北。
经过这番密谋,沙皇政府决定:首先要保持中国北方的“战前状况”。为此,沙俄把德法两国拉到自己一边,演出了一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的活剧。《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沙皇政府向德法两国正式提出建议,为了吸引德国参加“干涉”的行列,沙皇政府确是煞费心机。它竭力窥测德国对远东政策的真实意图,施展手腕拉拢德国。德国此时正想方设法在远东伸张侵略势力,迫切要求在中国取得一个海军基地,不愿日本过于强大,以致妨碍德国对远东的侵略扩张。
现在,沙俄迫切需要德国的帮助,如果这时答应共同行动,就可一举两得:一则可以“转移俄国的视线于东方”,即把沙俄这股祸水引向东方,松弛俄法同盟关系,减轻对德国的压力;二则可以作为中国的“恩人”,从中国割占一个海军基地。沙皇政府摸准德国的意图,特意作出了保证德国边境和平等诺言。彼此各有打算,终于暂时又相互勾结在一起了。
法国本来就是沙俄的同盟国,它参加对日干涉的行列,既可以显示对盟国的支持,又可以借此向清朝政府邀功索赏,扩大在中国的殖民势力。沙俄在串联德法两国的同时,继续调兵遣将,加强三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四月二十日,沙俄在海参崴实行“临战地区戒严令”,阿穆尔地区的军队“已接到出动准备的命令”。
结语
在沙俄策动下,三国坚持要求日本全部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为了不致丧失从中国夺取的其他侵略利益,终于在五月五日向沙俄等三国声明,接受“劝告”,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沙俄得悉日本五日声明后,认为“干涉”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便一变原先劝告清朝政府暂缓批准条约的态度,转而压迫清朝政府按期同日本换约。五月八日,清朝政府被迫同日本完成了换约手续。
参考资料:《满洲通志》《维特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http://www.592taotaole.com/bmrhzl/9903.html